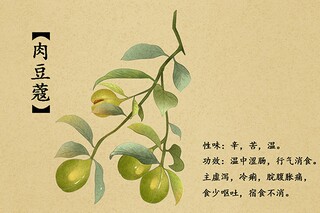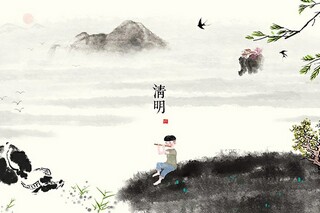
诗歌及语言的关系
“诗歌语言”与“诗歌言语”并非一回事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。
有人说:“诗歌语言”是物象间的“有机化”、“戏剧化”的神秘联系;其中,“有机”寓意着神差鬼使的“合理”与非尔不可必然,“戏剧”则是指出人意料之外的艺术变数。因此得出结论,较之大众语言,“诗歌语言”是“物与物”联系,而不是“词与词”的联系;理由是物具生命性而词不有。
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,历史悠久的中国诗界及诗歌教学对诗歌的讨论与研究,几乎长期都是以“诗歌”整体来替代“诗歌语言”局部。更没有去深挖掘“诗歌言语”这个“宝”。
其实“语言”与“言语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因此,“诗歌语言”与“诗歌言语”也不是一回事。而“诗歌”,则一个整合概念,又具有其自身的完美性。
诗歌
“诗歌”是最古老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,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。
“诗歌”这种文学样式要求高度、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,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。
“诗歌”在行文书写上,一般要求分行排列。在言语方面,“诗歌”拒绝语句在说或者写上拖沓冗长,而要求精炼、形象。
“诗歌”最具文学特质的地方就是能自成一格,且能跟其他艺术结合到一块并融入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之中,成为其他艺术形式表现上魅力绽放的“瑰宝”。譬如,散文诗、歌词、诗剧、圣诗等,文字配上音乐,就成了可以被人们相互传唱的“歌”。
语言
“语言”是音义符号体系,是一种交际工具,人们借助之来保存并传递人类文明成果。
“语言”是民族的表征之一。不同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。世界上的主要语言有汉语、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;其中,汉语使用人口最多,英语使用最广泛。
人们交流思想使用“语言”,因此“语言”起着一种重要的媒介作用。
言语
“言语”是“语言”的具体运用及运用结果。因此其含义有二:
1、运用“语言”,即“说”或者“写”及其相对应的“听”或者“读”——这么一种表述与理解的过程。
2、“语言”运用结果,即口头的或书面的言语作品,系言语活动的结果。
关于“语言”与“言语”二者的概念上的区分,源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.德.索绪尔(FerdinanddeSaussure,1857—1913)的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(1916)。
再看“诗歌”、“语言”、“言语”三者的关系,足以发现:
“诗歌”是人们运用“语言”的结果,展示了人们的“言语”,是人们“言语”的一部分。
因此,假如“诗歌语言”=“诗歌”+“语言”的等式关系成立,则可以推论出“诗歌语言”=“言语作品”+“媒介”这样的一个等式关系;其中,“后一个等式关系中的‘言语作品’指代的是“诗歌”,“媒介”指代的就是“语言”。
因此,“诗歌语言”是诗人借以抒发情怀而成就诗歌的必不可或缺的言语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诗人的言语风格。
那么,是否可以对“诗歌言语”做“诗歌+言语”这样的等式化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但是以此再进行等式化,则成了“言语+言语=‘言语’+‘言语’”,即“言语”=“言语”。
而“言语”=“言语”,在形式逻辑学上显然是一种循环定义错误。所以,有“诗歌语言”说而无“诗歌言语”说则无可厚非。
实际上,“诗界及诗歌教学”在研讨诗歌时,针对的是“诗歌言语”;因为只有“言语”才具有“交流功能、符号功能、概括功能”。
研讨诗歌在于其“言语”,而不在于其“语言”;因为“语言”只是“符合”、“工具”的。